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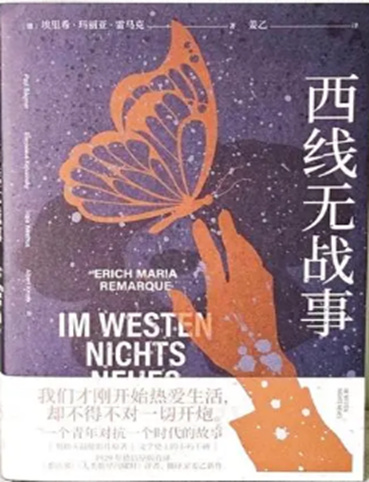
《西線無戰事》是根據作者雷馬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親身經歷書寫的一部小說。它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前方士兵的非人生活和后方人民的深重災難,對這場非正義戰爭提出了憤怒的控訴。全書主要是通過戰爭場面的描寫以及幾個戰士對戰爭的感受來揭示這場戰爭帶給人民的悲慘遭遇。根據小說改編的德國電影《西線無戰事》,在2023年的第9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中,一舉拿下最佳國際影片、最佳攝影、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原創音樂4項大獎。為了深入探討小說的主題內涵,西南大學師生展開對話。
“回憶”反襯戰爭的恐怖與殘酷
研究生何林芮: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是如何在戰爭中走向滅亡的?就讓無邊的大地,那曾保護過他們無數次的大地永遠擁抱他們吧!讓他們與蝴蝶起舞,與雀鳥共鳴,戰爭如此殘忍地奪取了這代人的世界,讓每個可貴的靈魂最后化成戰后清算中的一個數字。作者將現實與回憶穿插,使得戰爭拋離宏大敘事,鐫刻在保羅這個敏感脆弱的青春期男孩的內心,每當在大篇戰斗描寫推遠了普通讀者與主人公距離的時候,就會悄然浮現出他細膩柔軟的內心情感。請問您如何看待小說中的回憶敘事?
博士生導師董小玉:回憶作為一種特殊的敘事機制,不少優秀的中外文學作品中都有所體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文化界也越來越多地關注回憶話語模式。雷馬克在《西線無戰事》中也巧妙運用對前線冷峻客觀的描述當中,適當插入主人公的回憶細節,以此清晰地“展示了人物迷茫情緒形成的動態過程”。
初入軍隊時,保羅和他的同伴就感受到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從開始進入前線,到真正躲入隱蔽壕發動進攻時;當他們俯身貼在“支離破碎的褐色土地上”,每天目睹成批的人死去的時候,這反差日漸撕扯著他們的靈魂。在神經的持續緊張和極度恐懼中,一些士兵患上了幽閉癥,幾乎所有人到最后都處于崩潰的邊緣,開始對死亡感到麻木,甚至逐漸變得瘋狂而不顧一切。”冷漠、異化是殘酷的戰爭對人性摧殘到極致的表現,而這一切都通過雷馬克對前線戰場冷峻犀利的自然主義描述得以再現。
在炮火暫停的間隙,作者卻有意插入了主人公在前線放哨時對過往寧靜生活的回憶。透過照明彈的亮光,他仿佛看到了夏日夜晚,自己一個人待在家鄉的場景:那一排白楊樹,自己“坐在小溪岸邊的樹下,兩只腳蕩在清澈、湍急的溪流里”,感受“溪水純潔的香味和風吹白楊樹的旋律”。相對于前面大篇幅關于激戰、死亡和恐懼的直觀描寫,回憶性的文字以細膩溫婉的筆觸描繪了主人公曾經擁有的純凈美好的過去,也讓讀者緊繃的神經暫時得以喘息。
參與了前線戰爭的青年士兵終于明白自己不過是戰爭的“炮灰”,從失望到逐漸麻木繼而絕望。在小說主體部分插入的這段回憶與上下文不僅在敘事風格上形成鮮明對照,凸顯戰爭對人類生活的破壞,通過保羅的內心獨白和矛盾情緒,表達出戰爭對人精神和心靈上造成的創傷。這段回憶敘述雖然篇幅不長,但穿插在戰爭場面的描繪中卻是點睛之筆。
戰爭——大而無意義的深淵
研究生何林芮:雷馬克和許多偉大作家一樣,在經典誕生之前并未想過什么“暢銷”。這本僅15萬字的小說,淋漓盡致地描述了戰爭中士兵生活的悲慘和殘酷。小說自始至終貫穿著哀婉動人的筆調。結尾更是一唱三嘆,令人蕩氣回腸。柏林大學教授馬丁·霍博姆曾這樣評價:這部小說扣人心弦,真實,偉大。它像一部紀錄片那樣忠實于自然,被一位詩人感覺到并創作出來。藝術得救了……人類的良知,清醒吧!請問,您如何看待《西線無戰事》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
博士生導師董小玉:《西線無戰事》中既包括了戰爭實景的高度還原,也承載了太多沉重復雜的反思。雷馬克試圖用文字療愈創傷。這個過程必然是充滿艱辛和苦痛的,因為療愈的過程不僅需要“重返”煉獄般戰爭場景,還必須重新經歷青春理想的幻滅。雷馬克既是訴說者,也是見證者。一個沒切身經歷過戰爭的人,是無法將戰壕與炮火描寫得那般詳盡逼真的,他對戰友死亡情景的描繪可謂極于毫芒,令人驚心動魄。
在文學創作中,沒有與心靈無關的純粹客觀再現,也沒有與現實無關的純粹主觀表現。然而,《西線無戰事》將表現與再現加以結合與純熟運用。小說有“我們既像小孩子被遺棄,又像老年人有豐富的經驗,我們粗魯,又悲傷,而且膚淺——我相信,我們毫無希望了。”這樣直白表述迷惘一代翻涌而至的情感;也有“生活僅僅是在暗中守候死亡的威脅——它把我們變成有思維的動物,以便把本能的武器交給我們,它把麻木不仁灌輸給我們,使我們在恐懼面前不致崩潰……”這樣比喻性和指代性明確的事實,并將這一事實漸漸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作者將戰爭所帶來的精神痛苦刻畫得比皮肉之苦更入木三分。
為什么這樣一部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能夠幾十年屹立不倒?其永恒的生命力在于透過文字,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誠如《紐約時報書評》:戰爭把雷馬克打造成一個偉大的作家。他無疑是一流的巨匠,能讓語言向他的意志臣服。無論是寫人,還是寫沒有生命的自然,他的筆觸都是沉著、敏感和自信的。雷馬克正是以這種“語言的痛苦”渲染了戰爭這個大而無意義的深淵,令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不寒而栗、唏噓不已。
小說封面上寫道——“我們才剛開始熱愛生活,卻不得不對一切開炮。”令人反思戰爭的骯臟,控訴戰爭的非人道。小說最后寫道:“1918年10月,他倒下了。那天,整個前線是那么的安靜,乃至軍隊報告上只寫了這樣一句話:西線無戰事”。這一個回環,既呼應了小說的標題。雷馬克是懷著對和平的時光充滿柔情和眷戀的心境,寫下《西線無戰事》這部驚世駭俗的小說,以此來捍衛他心中神圣的和平與人的尊嚴,以此來紀念不計其數地溶解在戰爭中的青春。
文/董小玉 何林芮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