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涂涵鈺
《初識(shí)傳播學(xué):在信息社會(huì)里正確認(rèn)知自我、他人及世界》是一本經(jīng)典教材,由傳播學(xué)者埃姆·格里芬根據(jù)他在美國(guó)惠頓學(xué)院數(shù)十年的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撰寫(xiě)而成,先后經(jīng)歷多次再版。它的第七版由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展江譯介成中文。在《初識(shí)傳播學(xué)》中,格里芬教授不僅對(duì)32種傳播理論進(jìn)行了脈絡(luò)清晰、深入淺出的講解,還鏈接了新聞傳播學(xué)理論的學(xué)術(shù)前沿,為新聞傳播學(xué)學(xué)子提供專(zhuān)業(yè)教育的同時(shí),也致力于加深普通人對(duì)傳播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和重視,將傳播理論轉(zhuǎn)化為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更好地理解在信息社會(huì)中人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處理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在信息時(shí)代更好地應(yīng)對(duì)各種挑戰(zhàn)。為深入體會(huì)該書(shū)內(nèi)涵,西南大學(xué)師生就此展開(kāi)對(duì)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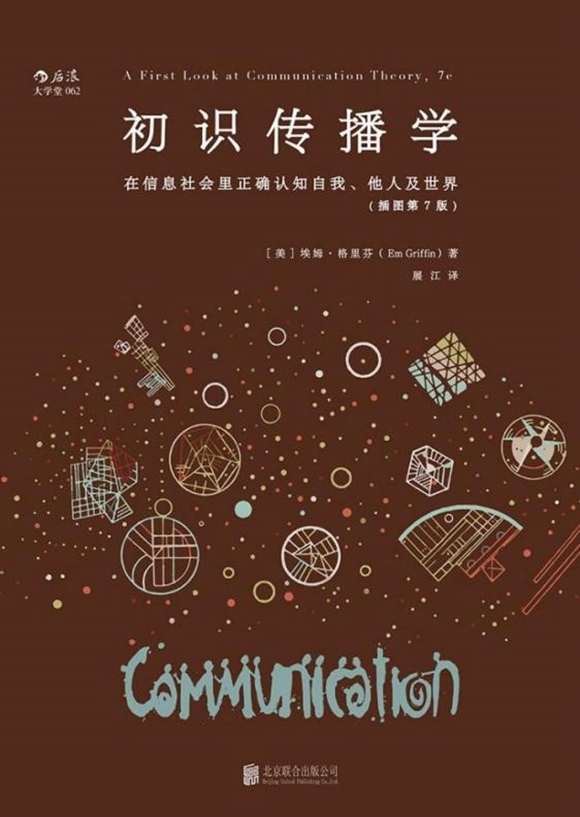
研究生涂涵鈺:在《初識(shí)傳播學(xué)》一書(shū)中,作者從傳播學(xué)七大學(xué)派出發(fā),先后向讀者介紹了32種傳播學(xué)理論,包含了人際傳播、影響力、群體和公共傳播、大眾傳播和文化語(yǔ)境五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結(jié)合當(dāng)下的媒介環(huán)境,請(qǐng)問(wèn)這本書(shū)最觸動(dòng)您的地方在哪里呢?
博士生導(dǎo)師董小玉:《初識(shí)傳播學(xué)》所介紹的傳播學(xué)理論很全面,涵蓋了傳播學(xué)各個(gè)流派的重要思想,時(shí)間跨度也非常大:從世界大戰(zhàn)時(shí)期、傳播學(xué)剛剛興起時(shí)有關(guān)人際互動(dòng)和影響力的相關(guān)理論,到千禧時(shí)代,人類(lèi)面對(duì)計(jì)算機(jī)和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而開(kāi)始的對(duì)技術(shù)反思等,這些理論對(duì)當(dāng)今社會(huì)有著深遠(yuǎn)的意義。如今,媒介技術(shù)的變遷是有目共睹,它在我們每個(gè)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年2月15日,Open AI發(fā)布的人工智能文生視頻大模型Sora推出后,再一次引發(fā)了人們對(duì)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的熱議。從ChatGPT對(duì)人類(lèi)語(yǔ)言的逼真模仿,到Sora對(duì)線下場(chǎng)景的敏銳捕捉與創(chuàng)造,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未來(lái)人類(lèi)與技術(shù)之間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這將重構(gòu)我們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認(rèn)知圖景。正如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家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所說(shuō):“計(jì)算不再只是計(jì)算機(jī)和技術(shù),它決定我們的生存。”在這樣的語(yǔ)境下,《初識(shí)傳播學(xué)》中對(duì)于傳媒生態(tài)學(xué)的理論介紹值得我們深思。
長(zhǎng)期以來(lái),以美國(guó)實(shí)證研究為代表的“經(jīng)驗(yàn)主義范式”和以法蘭克福學(xué)派為代表的“批判主義范式”是傳播學(xué)領(lǐng)域的兩大主流研究范式。千禧年以來(lái),技術(shù)主義范式逐漸嶄露頭角。傳媒生態(tài)學(xué),現(xiàn)在學(xué)界多稱(chēng)為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正是在這一范式的影響下應(yīng)運(yùn)而生,提出了一系列的傳播學(xué)理論,而媒介環(huán)境學(xué)主要探討技術(shù)和技藝、信息模式和傳播編碼在人類(lèi)事務(wù)中扮演著主導(dǎo)角色。在麥克盧漢、波茲曼和梅洛維茨為代表的三代學(xué)者的不懈努力下,該學(xué)派的理論體系日臻完善。1968年,波茲曼在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會(huì)成立時(shí)指出“媒介環(huán)境學(xué)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訊息及訊息系統(tǒng)。具體地說(shuō),媒介環(huán)境學(xué)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rèn)識(shí)和價(jià)值。它試圖說(shuō)明我們對(duì)媒介的預(yù)設(shè),試圖發(fā)現(xiàn)各種媒介迫使我們扮演的角色,并解釋媒介如何給我們所見(jiàn)所為的東西提供結(jié)構(gòu)。”
在《初識(shí)傳播學(xué)》中,作者著重介紹了麥克盧漢的相關(guān)思想,例如“媒介即信息”這一關(guān)鍵論斷。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huì)關(guān)注媒介傳遞的內(nèi)容,而忽略了媒介本身,對(duì)此,麥克盧漢指出:“媒介內(nèi)容就像是竊賊手中鮮美多汁的牛肉,其用途是分散思想領(lǐng)域看門(mén)狗的注意力。”與該觀點(diǎn)的邏輯起點(diǎn)相似,傳媒生態(tài)學(xué)正是將長(zhǎng)期以來(lái)被人們所忽略的技術(shù)與媒介作為研究的重點(diǎn),把媒介作為環(huán)境展開(kāi)研究。在當(dāng)下,媒介與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使其從不可見(jiàn)的黑暗中彰顯出來(lái),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成為傳播學(xué)研究的熱門(mén),同時(shí)也呼喚著大眾在日常的媒介實(shí)踐中,重新認(rèn)識(shí)媒介和技術(shù)所發(fā)揮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并警惕技術(shù)給人類(lèi)帶來(lái)的威脅,正如波茲曼所說(shuō):“每一種技術(shù)既是包袱也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后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chǎn)物”。
研究生涂涵鈺:《初識(shí)傳播學(xué)》的書(shū)皮上有這樣一句話——“在信息與人類(lèi)須臾不可分離的今天,傳播學(xué)是人人都必須掌握的一門(mén)藝術(shù)。”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diǎn)?
博士生導(dǎo)師董小玉:這是一個(gè)前所未有的時(shí)代!手機(jī)成為我們與家人朋友保持聯(lián)系的紐帶,短視頻讓我們足不出戶(hù)就能洞悉世界各地的新聞動(dòng)態(tài)。在這個(gè)互動(dòng)的世界里,我們可以獲得陌生人的點(diǎn)贊,也可以對(duì)他人的行為進(jìn)行點(diǎn)評(píng),我們是觀看者,也是參與者。直播、爆料、數(shù)字經(jīng)濟(jì)、虛擬現(xiàn)實(shí)等等新鮮體驗(yàn)已變成我們生活的常態(tài),然而,這些改變?yōu)槲覀兊纳顜?lái)便利的同時(shí),也引發(fā)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失落,正如海德格爾所說(shuō):“人們?cè)诩夹g(shù)座駕的逼促下按照技術(shù)的邏輯來(lái)遮蔽世界。”
而這一切,都與傳播學(xué)息息相關(guān)。對(duì)于智能化時(shí)代中的每一個(gè)人而言,學(xué)習(xí)傳播學(xué)是在一個(gè)全新的“信息國(guó)度”中,學(xué)會(huì)一門(mén)能夠幫助你暢游其中的重要工具。當(dāng)我們了解到傳播的規(guī)律和發(fā)展邏輯之后,其生活將會(huì)變得更加自如,以享受技術(shù)帶來(lái)的便利。正如喬姆斯基所說(shuō):“新媒介成為人類(lèi)解放的工具還是支配人類(lèi)的工具,關(guān)鍵看媒介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不僅如此,學(xué)習(xí)傳播學(xué)還能夠教會(huì)我們?nèi)绾卧谥悄芑鐣?huì)中保持理性。面對(duì)網(wǎng)絡(luò)暴力、群體極化、隱私泄露等媒介困境,學(xué)者們常常會(huì)提到公眾媒介素養(yǎng)提升的重要性,以《初識(shí)傳播學(xué)》為代表的傳播學(xué)科普書(shū)籍則能夠幫助民眾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yǎng)。艾呂爾認(rèn)為,不應(yīng)該用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取代道德標(biāo)準(zhǔn),而應(yīng)該用道德標(biāo)準(zhǔn)來(lái)應(yīng)對(duì)技術(shù)。在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技術(shù)倫理問(wèn)題不斷涌現(xiàn)的當(dāng)下,公眾對(duì)傳播學(xué)的認(rèn)知同樣也將幫助他們?cè)谛碌募夹g(shù)環(huán)境中保衛(wèi)人的主體性、捍衛(wèi)人思考和參與的權(quán)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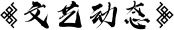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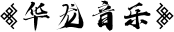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