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武輝夏
畫,僅止于技術(shù),那是凡俗工匠所為,真正的畫家,每作畫時,其實是在畫學(xué)問,畫修養(yǎng),畫氣質(zhì),畫格調(diào),畫感覺。惟其如此,才能知無功之功,知至道不煩,悉知其巧拙工俗,造微入妙而覺來信手筆有致。

著名人物畫家高濟民先生研習(xí)人物畫多年,探索不止,苦無所得。1986年偕筆者去九華山一游,與惟和法師邂逅,夜深相邀,促膝談禪。濟民聽惟和一夕禪話,似聞梵鐘震耳,漸生頓悟。此時,窗外一輪明月高懸空中,天清氣朗,萬物靜觀,真有一種正念即定、漸得自在的感覺。他兩眼似看非看,兩耳似聽非聽,凝神貫注,沐浴著寺廟燈火,赭石滲入石綠色的光輝,已是觀照默證,開合游藝、萬境自如之像。
特別是惟和法師說的:“兩手將大地山河捏扁搓圓灑向空中毫無色相,一口將先天祖氣咀來嚼去吞入肚里放出光明。”更讓高濟民認識到了“靜故了群動”的互補關(guān)系和“空故納萬境”的虛實空間在藝術(shù)上抒情達意的審美觀念。在大自然的神秘、朦朧氣氛中,求得了宏觀把握和微觀處理的統(tǒng)一,并進而得到了中國畫寫意人物畫在創(chuàng)新和繪畫意識方面的拓展,步入了心靈與宇宙意象兩境相入的華嚴境界。

他回到重慶后,心念神馳,筆耕不輟,興之所來,意到為止。逐漸在中國寫意人物畫方面得其奧妙,脫穎而出,形成了自己的個人風(fēng)格,成為了引人注目的畫家。
畫家高濟民應(yīng)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請,進京為天安門城樓作畫,精心繪制了《十八羅漢圖》,受到好評。隨后,高濟民受北京人民大會堂之托,再繪制兩幅丈二匹的巨幅作品,經(jīng)過半個多月的辛勤勞動,又創(chuàng)作了兩幅作品《十八羅漢圖》和《八仙過海》,兩幅作品均為潑彩大寫,“十八羅漢”和“八仙過海”都是中國人民熟悉而又倍感親切的傳統(tǒng)文化題材。

高濟民所繪羅漢別出心裁,獨創(chuàng)一格,既保留了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又對羅漢形象作了全新的闡釋,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現(xiàn)代意識和強烈的時代感,輕快、活潑、圓融、祥和。
《蕉下禪趣》圖,得益于五代禪僧貫休畫羅漢皆夢中所得的傳說。濟民畫一蕉下和尚掩衣裸腹,斜倚石桌前,一面品茶,一面看書,后背癢而輕搔之,以至于笑口長咧,既放松,又愜意的情狀令人看了不覺掩口而笑。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這種樂觀、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可以讓人在不愉快時,在遇到挫折時的情緒波動一一舒緩釋放,得到一種心理上的平和調(diào)整。

濟民說:“作畫技法中有寧方勿圓的說法,吾作畫,喜歡用圓筆,少用方筆,圓筆氣通,方筆氣阻,后研究陳老蓮時,方知老蓮青年時作畫多用方筆,年老后方見圓筆,所見略同也。”在《蕉下禪趣》圖中,濟民用圓筆一以貫之,不論和尚,不論蕉石,都畫得有一種圓融舒展的禪意,禪趣也在這種筆意中得到很好的表現(xiàn)。
濟民的仕女也畫得相當不錯,在中國繪畫史上,仕女畫也是人們喜聞樂見的題材。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唐代張萱的《搗練圖》,五代顧宏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作品均為國家級極品,后人無有超越者。此后,歷代仕女畫毫無發(fā)展建樹,多有纖弱媚俗之作。高濟民畫仕女則設(shè)色明麗,常以濃墨潑彩兼以精妙勾勒為之,力求高古恢弘,盡顯大唐風(fēng)韻,與時下流行仕女畫風(fēng)大不相同。

《觀畫圖》中,仕女品畫,我們觀賞此畫亦品美人,面前一盤紅果香甜可口,將三位畫中人的情態(tài)美感,映襯得格外引人注目。濟民在作此畫時,看得出是放筆直取,隨機應(yīng)發(fā),筆筆相隨,氣韻貫通,色墨構(gòu)成,線韻構(gòu)成,意象構(gòu)成。均恰到好處,簡潔,明快,和諧。
《畫壁圖》,濟民先生不拘古法,偏要讓禪定后的達摩坐歪身軀,以動制靜。既有觀照明凈,斂心跌坐之形,又呼之欲出,有凡人的生趣活態(tài),似乎說真要入定,做到于世海中,一毛發(fā)事,泊然無著染,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也真非易事。
《鐘馗圖》以潑墨大寫,描繪了龍須虬髯,身佩寶劍的鐘馗在茫茫的夜色中巡行的畫面。用筆既有方棱橫刮的凌厲之風(fēng),又有輕緩藏鋒的渾厚之氣。金剛怒目,令惡者見惡而懼之;樸拙親切,令善者見善而趨之。層次豐富,內(nèi)涵堅挺,很具神韻。

看了這些畫,我不禁想到宋代梁楷的《潑墨仙人》,又似乎見到了法國雕塑大師羅丹的《巴爾扎克》等作品,他們的作品都有不拘寫實寫形,而著重追求不似之似的神韻。離形得勢,離勢得趣,離趣得性。
蘇軾在一首詩中寫道:“論畫與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濟民先生的人物畫,多取材于神話傳說中人物,濕筆暈染,一揮而就,筆下人物既有又無,既無又有;既實又虛,既虛又實。渲導(dǎo)氣韻,驅(qū)遣情志,強調(diào)抒發(fā)個人內(nèi)心世界的真實情感。表現(xiàn)心靈力量的超越,體現(xiàn)了他強烈的藝術(shù)個性。

著名美學(xué)家李澤厚說:“頓悟的快樂,比起那強烈刺激的痛苦與歡樂的交響詩來,它似乎更能長久地保持某一種詩意的溫柔牧歌的韻味。而它所達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悅也是一種似乎包括愉悅本身在內(nèi)部消失溶化的那種異常淡遠的心境。”西方藝術(shù)大師羅丹也講到了一種“大清明”的境界:“藝術(shù)就是靜觀、默察;是深入自然,滲透自然,與之同化的心靈的愉快;是智慧的喜悅,在良知照耀下看清世界,而又重現(xiàn)這個世界的智慧的喜悅。”自然之光照亮外界,精神之光照亮自身,“徇耳目內(nèi)通而外于心知”是內(nèi)視內(nèi)聽,靜觀默照,虛靜的境界就是精神之光照耀自身的境界。
濟民畫禪,不僅僅只為畫畫,他把作畫的過程本身當成一種體驗,對靈魂凈化的過程,沒有體驗,就沒有意趣,同樣也沒有藝術(shù)的產(chǎn)生。濟民的畫是哲學(xué),又是生活。他力圖用整個生命去詮釋的東西,帶給人們的卻是人世情感真善美的追求。

“悟時剎境是真心。”拈花微笑的禪是禪悅,這種高峰體驗的歡悅具有一種遍及宇宙或超凡的隨和性質(zhì)。它完全稱得上幸福愉悅,生氣勃勃,神采奕奕。既以人類的渺小(虛弱)為歡樂,又以人類的偉大(力量)為歡樂。在這種意義上,它既是成熟的又是童真的,是一種縱橫自在的超越。高濟民的畫正是他本心的具有悠遠韻味的那種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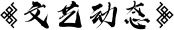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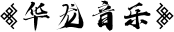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