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鐵城
掐指算來,與鼠“斷交”已有整三十年了。
那是1994年,我所在的單位蓋了一幢職工集資樓,按職級、工齡和其他擇房條件,我有資格挑選三至十樓的任意一套住房。
然而,為了徹底與深惡痛絕的鼠“斷交”,我毅然選擇了一套十五層以上的房屋。
起因是自記事以來,到分配此房之前的三十三年間,我曾與鼠打了無數次“交道”,并與之進行過反反復復的不懈斗爭。
想起與鼠斗的前后經歷,至今仍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真正與鼠“斷交”后,我又深感釋懷,不時向身邊的朋友們調侃道:“與鼠相斗雖無共贏,但總覺其樂無窮!”
提起鼠,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鼠目寸光、賊眉鼠眼、膽小如鼠、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等關于鼠輩的眾多詞匯。
本文所述之鼠,確系在實際生活中相遇、相交過的真正的鼠。
在短暫的人生旅程中,我曾與鄉村鼠、集鎮鼠和都市鼠等三類不同地域的鼠打過“交道”。
青少年時期相遇的鄉村鼠,因父老鄉親個個缺衣少食,鼠輩也跟著挨餓遭罪。鄉村鼠個小體瘦、豎長、黃毛、膽小怕事,可頭腦反應極快,動作靈敏迅疾。由于長期食不果腹,藏于洞中害怕見人。因此,鄉村鼠才是人們常說的賊眉鼠眼、膽小如鼠的鼠。
與鼠真正意義上交惡,是在我五歲那年夏天的一個晚上。
那天夜里,因白天貪玩疲累得一塌糊涂的我,上床就進入了甜蜜的夢鄉……
正待我樂呵呵地,即將從玩伴手中接過最喜吃的麥粑時,一陣劇痛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慘烈的哭叫聲,將忙著家務的父母、哥姐招到了床前。
母親忙不迭地掀開蚊帳,就著昏暗的油燈一看,我滿臉鮮血不說,眉宇間自上而下還有一條冒著鮮血的傷口。
鬧了半天,大人們才明白:原來是在我枕邊覓食的鼠,不知遭受啥驚嚇后拔腿開跑時,鋒利的鼠爪將我眉宇蹬出了一條近兩厘米的傷口。
時至今日,當年被鼠蹬傷的地方,仍留有一道明顯的痕印。
從此之后,我內心深處就十分痛恨賊眉鼠眼,嚙食糧柜偷吃糧食的鼠。
懵懵懂懂的我,背著大人花錢買回釣魚鉤、線,試圖將鼠釣到后在父母面前逞逞能!
怎么也沒想到,我耗錢、耗時、耗精力的用心之舉,卻慘遭鼠輩的不管不顧和不理不睬。
后來才知道,鼠十分靈巧敏銳,一般情況下,它們不會輕易上“鉤”!
相遇集鎮鼠,是1981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
為盡力搞好自籌自辦的公社文化站,我主動向縣文教局領導提出,將分居兩地的妻子,從城里調到鄉下的公社中學后,學校領導在房屋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騰出一間近四十平米的教室,作為我一家三口的住房。
說是教室,其實是一間寺廟廂房。
當年的龍河中學,曾是遠近聞名的徐家寺。
此前的徐家寺,是當地人們逢年過節祈福祭祖、上香拜佛的一座歷史悠久、古色古香的寺廟。徐家寺分上下殿和左右廂房,我的家是右廂房。旁邊,還臨時搭建起兩間近百平方米的學生寢室,常年居住著四五十名住校生。
正因有那四五十名住校生,我所相遇的集鎮鼠不為吃喝發愁,長得肥頭耷耳,走起路來漫不經心,還像鴨子一樣左右搖擺……
集鎮鼠肥頭耷耳、大模大樣的派頭,讓人看上去很不是滋味。
肥碩白胖的集鎮鼠惹我煩惱,源自鼠輩“狗改不了吃屎”的秉性。
鼠系嚙齒類動物,哪怕它們一日三餐不缺吃喝,仍改不了嚙食人類家具的秉性。據說,鼠一天不嚙吃東西,它們的牙就會癢癢得難受至極。
盤踞于我家陰暗之處的鼠,不分白天黑夜,瞅準我和妻白天上班或深夜熟睡之機,肆無忌憚地嚙食衣柜、床頭柜以及我那心愛的三抽柜。
七八十年代的家具,基本上都是由床、衣柜、平柜、三抽柜和梳妝臺、飯桌等六大件組成。條件較好的也配置有角柜、櫥柜和洗臉架之類附屬家具。
對于自小就喜歡讀書的我來說,三抽柜當仁不讓地成了心愛之物。
三抽柜長一米二,寬八十、高九十公分,由一大兩小三個抽屜和一個柜子組成。
我家的三抽柜,既是書架和書柜,又是寫字臺。
那時的我,總是將一個簡易書架靠墻擺放在三抽柜柜面,把常用書籍分一二三排陳列于書架。不常用需保存的書籍,就一股腦兒裝進右下方的柜里。
十分惱怒的是,搬進學校那個家不足半年,三抽柜、衣柜和床頭柜均被那群可惡至極的集鎮鼠嚙食得千瘡百孔、慘不忍睹。
更讓我氣憤之極的是,當我打開書柜,搬出存放在柜中那些不常用的書刊時,竟發現多部書刊都被鼠嚙食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第二天,忍無可忍的我,便獨自一人悄無聲息地到供銷社生產資料門市部,買回了十幾包老鼠藥,神不知鬼不覺地放置到鼠們經常出入的地方,喜滋滋地靜候著鼠輩“全軍覆沒”的佳音。
一天一夜過去了。
兩天兩夜過去了。
三天三夜過去了。
信心百倍、滿懷希望的我,除撿到一只幼鼠死尸外,壓根就沒看到鼠輩“全軍覆沒”的喜人局面。
夜深人靜時,鼠依舊成群結隊地嚙食著家具。我卻一聲不吭地躺在床上,苦思冥想著怎樣收拾它們!不時,也會將床頭板拍打得震天響,將鼠們嚇得屁滾尿流、魂飛魄散。
如此這般堅持了一段時間后,耿耿于懷的我,花五十元巨資在街上購回五個捕鼠神器“逮鼠夾”,不吭聲不出氣地悄悄將“逮鼠夾”擺放于鼠輩的必經之地,又一次高枕無憂地靜候著佳音。
事實證明,“逮鼠夾”真是名不虛傳。不到半天時間,就有兩只大鼠中了招。
為泄憤,我將逮鼠夾夾住的兩只大鼠取下后,用事先準備好的繩索綁牢,掛在家門前“示眾”,以此震懾震懾其余鼠輩。
正興致勃勃地憧憬著日后巨大捕鼠成果時,我們兩夫妻便接到了調離公社中學的正式通知。
進城后,我又遭遇了見過世面、趾高氣揚,皮囊發亮、油光水滑,人前人后從不賊眉鼠眼的都市鼠。
城里的新家是底樓,房前有口化糞池,房后有條餐廚下水道。其地理環境,很是適宜鼠輩生存和繁衍。
那些見過世面,膽大妄為的都市鼠根本不怕人。無論是白天和黑夜,它們都會成群結隊,大搖大擺地進進出出。
一天中午,幾個鄉下來的朋友正在客廳品茶談事。我下意識地看到四五只鼠在客房門口張望,試圖橫穿客廳通過主臥翻窗而出。
見此情景,我用力將腳在地上一跺,本想將鼠嚇回客房鉆入洞中。
哪曾想,聽到跺腳聲的鼠們,非但不掉頭回客房,反而目中無人飛也似的“呼、呼呼”穿過客廳和主臥,翻越窗戶跳到了房外。
被鼠情驚擾得有些目瞪口呆的鄉下朋友,緩慢地回過神來苦笑著調侃說:“你們城里硬是不一樣,連鼠都與眾不同,膽識過人。”
最讓我忍無可忍的是,鼠們鳩占鵲巢,膽大包天地在我新買回的三抽柜里繁衍生仔!搬進新房不久,我就發現城里的鼠,比鄉村和集鎮還要多。又悄悄買回鼠藥和鼠夾,如此這般地“施計”和“布陣”,可從沒收到過丁點兒效果。
畢竟,此次相遇的是一群見過世面的都市鼠。
一天深夜,我忽然聽到少有人出入的客房里,傳來了一陣陣“唧、唧唧”“唧、唧唧”的仔鼠聲。
進客房認真查看后,才發現鼠窩就在書柜里,仔鼠的“唧、唧唧”聲,也是從書柜里傳出來的。
接下來,我就親自策劃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捕鼠之戰。
一天晚飯后,我輕手輕腳、不聲不響地摸黑躺在客房床上,睜大雙眼屏住呼吸,恭候著鼠們到書柜聚會。
不足半個時辰,就有七八只肥碩光滑、皮囊發亮的鼠依次從早已嚙食出的洞里鉆進了書柜……
待鼠們狂妄至極地在我心愛的書柜里尋歡作樂時,我不聲不響猛地一下翻身起床,迅疾用雙手左右開弓,一只手用事先備好的舊衣服堵住洞口,一只手用編織袋自下而上套住柜門。然后慢慢地將柜門拉開一條縫,一手緊攥編織袋口,一手用力拍打寫字臺臺面。隨著“呯、呯呯”的敲打聲,柜里亂成一團的鼠們,慌不擇路地朝著編織袋魚貫而入,悉數成為甕中之鱉。
大獲全勝的我,喜形于色地將裝有八只巨鼠的編織袋放到小區空地上,引來近兩百名鄰居圍觀。
與我一墻之隔的鄰居汪武,趕忙拿出自家的秤一稱,八只鼠竟足有五公斤重,頓時將圍觀的人們,一個個驚得瞠目結舌。
三十年過去了,基本與鼠“斷交”的我,不時回想起那些時日與鼠之斗的歷歷往事,仍有一種喜不自禁、其樂無窮的快感。靜下心來仔細一想,人鼠之間為啥會長此相斗,永無寧日?其因恐怕就是鼠輩生性好吃懶做,不勞而獲。除此之外,是因為鄉村、集鎮和都市,仍有鼠輩生存繁衍的洞穴和環境。
(作者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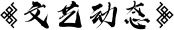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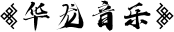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