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海燕
《國語》云:“蓄力一紀,可以遠矣。”有一條時間的隧道,見證了我十二年的光陰,它或者是120公里/小時的油門加速,也或者是方向盤切線15度角的換道超車。它串聯著我于理想的勁頭,又牽扯著我對回家的渴望。一邊是速度,一邊是速度的褶皺。
一條名為涪豐石的瀘渝南線高速公路,像一尾游弋在巴山渝水間的巨龍,以110公里的身姿串聯起涪陵、豐都、石柱三城,將千年江濤的沉吟奔涌與新時代的波瀾壯闊編織成山河間的經緯。我在這條瀘渝南線高速公路上驅車已經行駛了33萬公里,它記錄著我的人生、我的黃金時代。
黃昏時儀表盤的數字攀上三位數,后視鏡里那輪熔金的太陽照耀著我,碎成千萬粒光斑在擋風玻璃上流淌。我的車如一支離弦的箭,切開暮色稠密的重圍。彈指一揮間,我來這座城已經十二年了。
十二年前,我帶著人生美好的價值追求,來到這座城,這座在歷史上因三次更名而名動天下的豐都城。東漢的平都縣是豐都設縣之始。第一次更名是隋文帝楊堅來到平都縣,后詔改“平都”為“豊都”;第二次更名是明太祖朱元璋,下詔改“豊都”為“酆都”;第三次更名是1958年周恩來總理視察豐都,改“酆都”為“豐都”。這三次更名,是豐都歷史發展的沿革,是考究豐都民俗文化歷史的依據。
文字是歷史的見證者,有時候一個字就承載著一部文化史。我特別慶幸來到這樣一座“圣地由來遠播名,簡牘千年印記明”的神奇之城。好像總有探究不完的話題與神秘,等待今人、后人去永無止境地思考、假設、討論。有人說,世間的哲學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此岸的,一種是彼岸的。而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念世界是至善,這一點上,千年福地、尚善之城的豐都是擔得起的。豐都不止一面,它有多面。比如蘇東坡筆下的天下名山,酈道元筆下的平都福地,基辛格筆下的中國神曲之鄉。
路,是時間的詩行。而涪豐石高速公路,正是這首時間詩行中最美的篇章。它成為了我最忠實的文化擺渡者。十二年前我沒想到會來到一座城。有些人會為了一次心曠神怡的旅游來到一座城,有些人會為了一個激動人心的展覽或者一場美妙悅耳的音樂會跑到一座城,而我為了實現人生價值奔赴了一座城。
記得十二年前從九龍坡剛來到豐都,一個領導非常關切地問我:“你怎么從米兜跳到糠兜?”我開始還沒聽明白,后來又有一個領導問我,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為了實現價值。”讀書入仕濟民,這是古代讀書人最宏大的夙愿。西方哲學家尼采的名言“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如雷貫耳、影響深遠。有時候總覺得人生應該折騰一番,即便是從米兜跳到糠兜,老了回首時也會沒有絲毫遺憾。
有一年,母親60歲生日,我第一次沒能陪在母親身邊給她過生,還正是六十花甲。當時在豐都工作忙完一天,才一下想起那天是母親的生日,那時我內心充滿了無限的愧疚感。一位我喜歡的作家說過,一個女子望向天空的時候,是孤獨得無法言說。我抬頭望向天空,不是孤獨是想家。那天天上的月亮若隱若現,腳下踏著豐都這片熱土,雷佳演唱的《人世間》“世間的甜啊,走多遠都記得回家;祝你踏過千重浪,能留在愛人的身旁,在媽媽老去的時光,聽她把兒時慢慢講……”在我耳邊回響,眼淚頃刻間奔涌而出、傾如雨下。
有的路已經成為一種經歷一種過往,不為那些如花似錦的心中的焰火,只為曾經無法出口落俗的留白。我愛父母,如我愛這方熱土。
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瀘渝南線這條高速公路上,我在豐都和九龍坡兩地之間行駛切換,經歷過極端的天氣,比如剛穿過一座隧道,高速行駛的車忽然就遇上了暴雨、大霧,什么都看不清,也無法靠邊停車。我也經歷過爆胎、甩尾這樣的千鈞一發、危急關頭,臨危不亂、不驚不怖地始終把穩車子方向盤,停在應急車道等待救援。十二年的光陰流轉,輾轉兩地,一邊是跨越山海、續寫熱愛的星辰大海,一邊是長夜里照我前行的父母永遠為我留著的一盞明燈。走了很久的路,卻發現選擇一條路走,不單需要乘風破浪的勇氣,更要不能回頭的清冷。
“世間須大道,何只羨車行。”人生有很多不可預期,正如同我從未想過我會來到豐都這座城。在這座城里,我實現了許多我從未預期的收獲、理想、價值。在每逢周末的夜晚,我會遙看璀璨的星辰,穿過這條高速公路的隧道、彎道、直道,想著王陽明《平山書院記》的含遠秋芳,想著蘇東坡“此身不覺到云間,日月星辰任我攀”的光景超忽,仿佛儀表盤的熒光將我的影子投射在蒼穹,那使命的星辰正從穹頂撒落。“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想起高適,想起千里白日、北風吹雪。
(作者系豐都縣文化和旅游發展委員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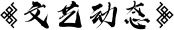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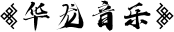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