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作為“社會公器”的公共性根基被日漸瓦解,公眾對于新聞行業的信心日漸流逝,新聞傳播的價值被質疑。在此情形下,當代美國新聞傳播學領域頗具影響力的學者邁克爾·舒德森所撰寫的《為什么新聞依然重要》一書,深入剖析了新聞業在新媒體時代的挑戰與前景,為當下新聞業的重要性進行了有力辯護。舒德森教授用歷史和比較的視野,一方面審視了新聞制作方式的迭代,另一方面,將新聞放置于政治語境中,探討了新聞與政治制度的互動關系。作者指出了新聞業的問題與前景,其知識社會學的關照路徑、民主理論與實踐的考察視角,為未來新聞業的何去何從提供了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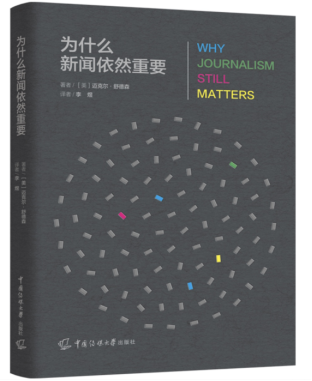
新聞是必要的,要將真相帶入公共領域
當今,技術門檻的消解與社交媒體平臺的興盛,賦予了新聞全新的樣態,也在無形中重構了新聞業。這種重構在降低行業準入門檻的同時,也引發了新聞生產的失序與專業權威的動搖。具體而言,信息生產權力的泛化稀釋了傳統媒體的權威性,虛假信息與嚴肅真相在算法邏輯中同臺競逐,公共傳播陷入“后真相時代”的混沌中;同時,流量經濟的支配性法則扭曲了傳播倫理,一些媒體為攫取注意力資源、獲得廣告收入,不惜采用隱私侵犯、標題操控與情緒煽動等“暴力”方式,解構了新聞的原有價值。在邁克爾·舒德森眼中,新聞業是一種特定的現代文化形式,它被慣例與實踐創造,被專業的組織完成。在報紙定期出版、普遍發行、面向公眾的產業成型過程,一種被稱為“公共領域”的社會結構應運而生,而新聞業秉持啟蒙運動的樂觀主義精神,堅持將真相帶入公共話語。
“真相是一系列協議,這是社會共識。”協議的一端是新聞生產者,另一端是社會公眾。過去提到的合格記者形象,多是跳脫出現實的獨立思考者。而正視記者不完善的知識框架和無法擺脫的權力干預,是正確審視新聞業危機的前提。舒德森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職業新聞人自我進化推動變革的敘事”不過是理想化的想象,真正推動變革的殘酷現實是——推崇舊有范式的老一代人消亡,新一代人掌握權力。
而作為新聞消費者的公眾,其自身的局限性似乎更難擺脫。人們傾向于相信他們喜歡的、給予他們希望的、符合先入為主觀念的、奉承他們所屬共同體的新聞。他們總是用預先的解釋和假設來看待事實,這使得離譜的謠言與夸張的謊言總能找到生存空間。在數字時代,這種認知偏好被算法精確捕捉并無限放大,最終將公眾馴化為自我證實的囚徒——人們既在主動篩選信息,又被算法反向塑造著認知框架。當情感共鳴的價值凌駕于事實核查之上,信息接收便異化為維系身份認同的儀式,真相最終被擋在了認知繭房外。真相一直面臨著四大強敵,即宣傳、利潤、偏見、惡作劇。這四大因素不斷阻礙著真相的傳播,讓我們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方向。
再筑“專業之壁”:準確、審思、故事
在互聯網這個信息野蠻生長的原始叢林里,新聞業如何通過專業水準與專業聲譽再筑“專業之壁”呢?舒德森在書中為新聞記者開出三劑良方:
一是準確,拒絕相對主義。“準確”一向被新聞界奉為圭臬,被視為不言自明的行業價值標準,我們要強調新聞事實信息的準確,要把事實與觀點區分開來。面對大數據編織的信息迷陣,專業性不是相對主義的折中,而是在事實中錨定真相坐標,因為“真實性是新聞業建構社會信任的核心契約。”
二是逆著自己的假設去做報道。這并非完全否定自己的感知、經驗和預判,而是在報道中多一份省思,將光照向認知盲區的褶皺,允許任何與自身價值觀和職業經歷相悖的事實發生。同時,邁克爾·舒德森指出,對話不能創造民主,相反,是民主創造了對話。
三是跟著故事走。真正的專業記者應是新聞長河里的“溯流者”,對事件的探索絕不能淺嘗輒止,要克服環境阻力和人為因素的影響,在保證事實核查的基礎上,沿著故事發展的脈絡一直跟蹤報道下去。這就要求記者關注當代生活,克服自身立場,用故事的呈現觸動人、改變人,這其中也包含著隱匿自我表達的分寸感。
邁克爾·舒德森深入剖析了新媒體時代新聞業的專業危機,對新聞業發展與商業主義的關系提出了深刻見解。他并未全盤否定商業化對新聞業的負面影響,而是以歷史視角剖析了商業驅動如何成為新聞業專業化、公共性轉型的核心動力。透過“市場失靈”的分析,他指出在商業主義進步的背后,新聞業階段性變革的本質:職業新聞人的權利更迭和社會環境賦予新聞業的職責演變。作為知識社會學家,舒德森以一種灑脫卻有理有據的姿態對未來的新聞業保持樂觀。他相信,新聞業無可替代的社會功能一直不乏現實主義的支持,未來新聞業也一定可以在社會發展中做得更好。
作者:董小玉、王碩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