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津菁
熊平安,男,1946年6月3日出生,四川遂寧人。國家一級演員,重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川劇代表性傳承人。中共黨員,重慶市川劇院演員,曾任副團長、副院長。1959年,熊平安考入北碚川劇團,1985年調入重慶市川劇院至今。熊平安從藝50多年,應功文、武小生兼文、武老生。師承李俠林、袁玉堃、受藝于鄒西池等老師。代表作有《柳蔭記》《玉簪記》《繡襦記》《禹門關》《呂布與貂嬋》《闞澤薦陸遜》《治中山》《反徐州》《絳霄樓》。整理、導演、傳授的劇目有《訪友》《踏傘》《摘紅梅》《逼侄》《琴房送燈》《畫蝴蝶》《海瑞》《赴考》《八郎耍路》《小宴》《鐵龍山》《登樓觀兵》《逼反武成王》《打瓜園》等。近十年來,導演的劇目有川劇《聶小倩與寧采臣》《金染坊》《連心橋》《辦酒》,石柱土戲《秦良玉和馬千乘》等等。

“無技不成戲”的演員時光
當熊平安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技藝對于一個川劇演員的重要性。只要有了精湛絕倫的技藝,就會有臺下排山倒海的叫好聲和鋪天蓋地的“巴巴掌”。這種至高的榮譽感值得讓一個獨生子舍棄優(yōu)渥的家庭生活進入戲班,也值得讓一個初出茅廬的俊小生熬盡歲月。
熊平安童年時的家,在重慶石板坡。他的父親經(jīng)營著一家醬油廠,小康殷實的家境讓熊平安能以欣賞藝術的方式走近藝術。父親經(jīng)常帶著熊平安去重慶大眾游藝園等地方看川劇。父親是個戲迷,卻不想讓自己的獨生兒子學戲。11歲,熊平安毅然決然地拋掉了舒適的家庭生活,去北碚川劇團享受那吃不盡的苦頭。
一進入劇團,老師們覺得熊平安演花臉或是演小生都是合適的。而熊平安更愿意演花臉,雖然小生瀟灑漂亮,卻沒有花臉“中洋”。何為“中洋”,就是更能討喜觀眾,會獲得更多掌聲。熊平安演了《張明下書》中的小花臉,還演了《喬老爺奇遇》中以褶子丑應工的喬溪和藍木斯。熊平安盡情地表達著川劇小花臉的詼諧和幽默,他用他“逗樂”的本領收獲了在藝術青春期中的第一捧玫瑰。

熊平安在老師們的要求下,也學了小生戲。有一件事讓他對“中洋”這件事兒有了新的體悟。他被團里派到鄉(xiāng)臺口去演出《下游庵》一劇。據(jù)熊平安介紹:“川劇《下游庵》是一部非常經(jīng)典的川劇劇目,也被稱為《盤貞認母》或《庵堂認親》。該劇講述了明代宦門子弟申貴生與法華庵女尼王志貞相愛,后申貴生死于庵中,王志貞生下一個遺腹子。這個孩子后來被徐知府拾得并取名徐元宰,撫養(yǎng)成人。徐元宰在得知自己身世后,前往法華庵尋找親生母親,經(jīng)過多次盤問,母子終于相認的感人故事。”熊平安飾演的盤貞(徐元宰)溫厚儒雅,深情款款,很受觀眾喜歡。但篤定小花臉更“中洋”的熊平安,并沒有認識到自己“小生”的價值。
這時,發(fā)生了一個“舞臺意外”。一次,《下游庵》演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被叫停。正在臺上演得難分難舍的熊平安一臉懵,卻只好下臺。原來,重慶某軍區(qū)大領導專程趕來看他的《下游庵》,卻因事耽誤了,趕到即遲到,只好讓劇團重新為領導演一遍。這段小插曲著實讓熊平安徹夜難眠:“說是好玩的小花臉吸引觀眾;這俊逸的小生吸引的可是大領導。”年輕的熊平安在反思著,為什么小生看似穩(wěn)重儒雅的表演,仍然會“中洋”呢?2018年,筆者曾邀請熊平安先生為國家藝術基金培育項目“川劇理論評論培訓班”上了一堂課《淺談川劇特技的運用》,在課上,熊先生曾用了大篇幅去講小生行的技法。他談到小生褶子功“踢”“頂”“勾”“蹬”“含”。我想,“大領導本尊到底是誰”這個問題可能在熊先生心中早已煙消云散,對“中洋”問題的再認識卻已經(jīng)深入骨髓了吧。在此后的幾十年里,他該是如何去追求小生褶子功的盡善盡美呢!他為了向同團的師兄劉明忠討教褶子功,主動把自己挺括高端而“棱角永不倒”的毛嗶嘰褲子借給劉穿。后來,熊先生告訴我說,原來,用小生的身法,去優(yōu)雅的、含蓄的、瀟灑的美著,在舞臺上也特別有力量,觀眾不是只喜歡笑的傻子,觀眾也很高級,他們除了愛笑,更愛美。

那么,盤貞之類的文小生是“中洋”的,武小生呢?年輕時的熊平安臉龐飽滿,扮出來的文小生可愛勁兒多于俊俏感,甚至有人戲謔他是“奶油小生”。他扮上武小生就不同了,寬額闊面,鼻子高挺,眉鋒飛入兩鬢,英武非凡。他著靠子,扮龍箭,又踢尖子、推衫子、耍翎子、提把子——熊平安深知武小生“中洋”的真諦是功夫硬,為了那個樸素的目標,他便拼了命地練起來。其實練好功夫,除了可以在觀眾那里“中洋”之外,還有其他獎勵,就是那個時代稀缺的食品。他時常一邊把腿放在把桿上使勁壓,嘴里一遍遍反復念叨“白糖”“高級餅餅”“白糖”“高級餅餅”……

他追求或“被迫”追求武小生極致技能的過往,成了生命中最刻骨銘心的領悟。“中洋”有時要靠命來換。那一次,他飾演《盜冠袍》中的白菊花,需要從三張桌子上翻一個“倒踢”下來。這個危險的高難度動作平時是難不住以膽子大著稱的熊平安的。劇團到銅梁演出,他出場后,突然發(fā)現(xiàn)三張桌子上多一個大約50公分高的腳箱,立刻被嚇住了。因為他從來沒有從這個高度下來過,心想一個閃失,或許會殃及性命。他咬緊牙關,念完了白菊花的那段臺詞:“外邦冠袍進,盜寶走一程。譙樓起三更,月暗星不明。投石把路問,四下無官兵。翻身把宮進,冠袍放光明。”他就開始爬桌子,三張桌子其實是布置的七層藏寶樓。白菊花上了藏寶樓,偷出冠袍玉帶之后,要從藏寶樓上一躍而下,以表武藝奇絕高強。而熊平安眼前的藏寶樓,要比平時演出中多了50厘米,他的腳打著顫,一步步往上爬,他的師父李俠林此刻幫他扶著桌子,他明白徒弟心中此刻巨大的恐懼,他輕輕地鼓勵道:“崽兒嘞,你不慌哈。點兒都不要‘拗’,往后倒就可以了。”看來加腳箱是李師傅沒有通過徒弟同意的突發(fā)奇想和故意為之。而在這時,他還在強調著動作要領。臺詞都說完了,人也爬上去了,戲大于天,這翻也要翻,不翻也要翻了。我想,當時年輕的熊先生可能已經(jīng)聽不到鑼鼓提示的聲音了,他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和心臟被破土的聲音——年輕演員要“中洋”,得要活生生地在心上長出兩支翅膀呢。心臟會流血,很疼,很驚悚,需要過命的勇氣。熊平安一個倒踢翻下來,站住了。觀眾席的巴巴掌快要把劇場屋頂掀翻了。我想事后李師傅或許給了熊平安一個擁抱吧,可是熊先生給我說的是,他再也不理他的師傅了,兩人終于破冰之后,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怨怒道:“我可是家里的獨兒呀!”按理說那一次演出是極度“中洋”的。可《盜冠袍》熊平安這輩子再也沒有演過,徹底封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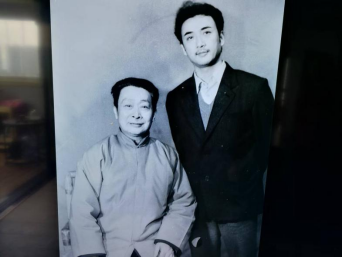
熊平安先生的主要演員時光,剛好卡在川劇由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時期。他早年多跟隨北碚川劇團活動在鄉(xiāng)土民間,和觀眾走得很近。他最知道川渝地區(qū)的川劇觀眾熱衷于什么。在傳統(tǒng)的民間的演出環(huán)境中,觀眾們熱衷于熱鬧、喜慶的演出和精彩絕倫的演員技術,有技術才能拿彩,奪眼球。因為和觀眾走得近,所以他深深地理解觀眾,他對技術的追求也都是為了觀眾。“中洋”一詞,本身就是演員與觀眾之間的情緒互動。一個演員只有心中有觀眾,演出為觀眾,才能走對自己的路。

熊平安演員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三個戲:《禹門關》《闞澤薦陸》《治中山》。許多文章已經(jīng)介紹了這三個作品,今天我不想多費筆墨。接下來,我想聊一聊熊平安先生的導演生涯。

“突破技術”的導演創(chuàng)作
作為一個戲曲編劇,筆者和熊先生合作了三個大戲。我想從我最熟悉的內容說起,講一講作為導演的熊平安,如何突破與升華他對“無技不成戲”的執(zhí)拗。我記得在和他合作的每一次,他都會說:“崽兒嘞,我已經(jīng)想到招兒了。”招兒是什么,如果演員是靠著過硬的表演技術(或絕技)拿彩,那么導演就是靠招兒了。招兒,是一個戲中最能展示戲曲舞臺魅力的形式路數(shù)和手法,能充分展示編導者的技術水準。在我們合作的三個戲中,這些招兒有的來自于傳統(tǒng)川劇,有的則是熊先生嘗試突破傳統(tǒng)而帶來的新穎創(chuàng)造。
首先來講川劇《金染坊》的明快節(jié)奏。
我倆合作的第一個戲是川劇《金染坊》。該劇被列入2017年度中國文聯(lián)青年文藝創(chuàng)作扶持計劃扶持項目,受到了中國文學藝術發(fā)展專項基金的資助。《金染坊》中最能展示導演技法的是“洞房”和“染坊”兩折戲。這個戲在舞臺呈現(xiàn)上最大的特點,是節(jié)奏的明快。
熊平安老師的導演讓這個戲的“明快”得以真正呈現(xiàn)。傳統(tǒng)川劇中有高腔戲《雙洞房》,而熊平安老師認為,傳統(tǒng)《雙洞房》并沒有把“雙”用起來。從我的劇本出發(fā),熊老師采用了“隔壁戲”的手法來表現(xiàn)《金染坊》“雙洞房”和“雙染坊”。隔壁戲能把“雙”用活。隔壁戲在川劇中多有出現(xiàn),比如由《醒世恒言·張廷秀逃命救父》改編而來的《雙杯記》中,就有一出“隔壁戲”。《雙杯記》中的隔壁戲是兩個人分別在兩個空間中的互動,他們彼此之間聽得到聲音。而《金染坊》的“洞房”則是兩對人分別在兩個空間中的互動,東和西兩個洞房彼此聽不見聲,看不到人,勾連兩個洞房的,是人物關系和情感。在喜慶而溫馨的過場音樂中,兩個洞房中的兩對情侶,各自表達:東洞房中展現(xiàn)的是成海的欲望和強勢與秋蘭的厭惡和反抗;西洞房中展現(xiàn)的是小五的熱情溫柔與月梅的順從和喜悅,此時的月梅還害羞地搭著蓋頭。直到小五把月梅抱上了床,才從醉意中醒來——自己娶到了不愛的人。于是懦弱的小五開始裝睡。兩個洞房呈現(xiàn)著相似的情境,卻是不一樣的氛圍。雖然有鑼鼓來打“情緒”,表現(xiàn)秋蘭的激烈反抗動作,卻經(jīng)過熊平安導演的悉心安排,而并沒有影響小五和月梅的溫柔動作。兩個洞房里的情節(jié)、情境、人物情緒都是相互對照、呼應、對仗、互文和反襯的。音樂、演員的動作都合理地闡釋著人物關系和戲劇矛盾。舞臺上的信息量大,兩個洞房讓人目不暇接。音樂有節(jié)奏、鑼鼓有節(jié)奏、人物情緒呼應也有節(jié)奏,故事在兩條相互平行又時而交錯的敘事線中激進推進。這樣的明快,其實是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上,超越了傳統(tǒng),導演在新的劇本創(chuàng)意基礎上,努力創(chuàng)造新的更為多元立體的戲劇空間去承載內容的信息量。什么叫明快,是戲劇結構支撐下,舞臺節(jié)奏的積極推進。和“雙洞房”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同一劇場節(jié)奏中,“雙染坊”表現(xiàn)的是兩對夫妻在東和西兩個染坊中,混雜在染布程序中的各自愛恨情仇的流淌。
其次來講實驗川劇《聶小倩與寧采臣》的老技活用。

2017年9月,我和重慶303話劇社的袁冶導演共同創(chuàng)作的實驗川劇《聶小倩與寧采臣》成功入選第十九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jié)“扶持青年藝術家計劃”委約作品。這個作品于當年10月24日,在上海戲劇學院端鈞劇場公演。為了托舉青年導演和編劇,熊平安老師是作為藝術指導,參與創(chuàng)作活動的。這出戲能在上海獲得火爆效果,我想至少有百分之五十,都是傳統(tǒng)川劇技術幫的忙。無論劇情怎么好,人物怎么鮮活,戲曲就是戲曲,外地人看川劇就是要看他的地方特色。熊老師反復給我說,這個戲要“吃著”,還得要上招兒。
熊先生一邊充分考慮劇情,一邊對落地表演技術進行甄選和打磨。這個戲的難度在于,袁冶當時是一位新銳的話劇導演,他要求的臺詞、節(jié)奏、格調都和傳統(tǒng)川劇有著很大的差別。在袁導的要求下,劇組采用了一種自由表達的思辨性的對話,認為這更能清晰地表達意義,更有戲劇沖擊力。而在我看來,這樣的語言“太實”“太滿”,不夠空靈,“留白”不足,很難加入有韻味的戲曲動作和身段。飾演聶小倩的吳熙也向劇組提出“這一段臺詞蒼白,戲曲味兒不足”的意見。然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選擇話劇臺詞的“充實”感,就得部分放棄戲曲的“靈動”美。為了在實的臺詞中,灌注戲曲身段和表演的空靈美,減少“話劇加唱”的阻塞感,熊先生也想盡了辦法,他至今還在和我念叨,那出戲中的“時空轉換”“偷桃符”“找曼陀羅花”幾個戲劇動作真是太難排了。
熊先生是一個真正開放包容的藝術家,在年輕導演甚至有些“難以理解”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面前,他選擇了敞開懷抱,支撐和托舉別人的自由藝術思維。為了讓這個戲更加精彩,褶子、水發(fā)、變臉的技術必須上硬貨。飾演寧采臣的青年演員張亮把川劇褶子功用到了極致,在劇情允許的情況下,熊先生生怕漏掉了任何一次能讓演員拿彩的環(huán)節(jié)。水發(fā)、背殼等川劇絕技一一展示。而飾演燕赤霞的文冬的表演驚爆了全場,他高超的武藝和松弛詼諧的表演令人難忘,他的變臉更是讓人目不暇接。來自全國各地的人看川劇,怎么能不看變臉呢?而這個變臉必須是一個“核武器”。別人變臉,臉就是一張不動的臉,然后等著變下一張;而文冬的變臉居然可以戴著一張鬼臉說話。我記得在化妝室里,某昆劇團的朋友來問熊老師關于水發(fā)和變臉的絕技時,熊老師笑盈盈的,卻沒答話。
我們合作的第三個戲是石柱土戲《秦良玉和馬千乘》,這是歌劇形式和戲曲手法的一次握手。
熊先生認為,土家歌舞的合理進入,是讓土戲更加輕快亮眼的絕好條件。事實上,傳統(tǒng)土戲是海納百川的。石柱土戲是集地方土家族文學、歌舞、說唱,民俗為一體的綜合藝術類型,在形成之初,就展現(xiàn)出開放的格局,它曾在發(fā)展過程中化用川劇、花燈戲等元素豐富自身。開放的形態(tài)為我們今天的創(chuàng)作提供基礎:一方面我們要挖掘傳統(tǒng)土家戲劇精髓;另一方面也要以開放的姿態(tài),吸收“活的”地方民族歌舞、文學資源,借鑒姊妹戲曲劇種的表現(xiàn)方式,融合加工成新“土戲”風格。
這個戲以“歌舞演故事”的方式,講述秦良玉年少時的動人故事,讓觀者感到,秦良玉的千古英雄豪情,是生長在石柱這片神秘美麗而又多彩多姿的文化之中,富有人情味,煙火氣,又生動美好。上述就是他對全劇的整體文化把控,我一邊贊同,一邊著手研究能為土戲運用的戲曲手法和少數(shù)民族藝術。土家玩牛、擺手舞、西蘭卡普的歌舞展示,作為開場,為該劇營造了熱烈歡快的氣氛。
在塑造人物階段,則化用了一些川劇的身法。例如秦良玉的舞劍、家院福四兒的身段等。秦良玉和馬千乘在船上的一段戲,則是化用了《秋江》的身法,《秋江》是陳姑和艄翁兩個人,而《秦良玉和馬千乘》則是秦、馬和艄翁三個人的戲。三個人在船上,浪起浪落,風雨飄搖,人間深情在一番江湖潮涌間漸漸流露,卻又裹挾著土家風情。通過這個戲的創(chuàng)作,我和熊先生的戲路更開闊了,交情也更深厚了。
從“無技不成戲”的演員狀態(tài),到“突破技術”的導演構想,我覺得有一種想法一直貫穿著熊先生的藝術生涯:為觀眾而做戲。行內人都說“戲比天大”,而其實比戲更大的絕對是觀眾。
當他還是北碚川劇團的一個年輕小生的時候,他就知道出挑的技術能“中洋”,能給觀眾帶去最大的享受。慢慢地,他明白了,“中洋”的背后是對各個行當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不吃千番萬般苦,就得不到精湛的技術。在當下,他成為了一位導演,眼界便又發(fā)生了變化,技術雖然重要,“濫用不是技”和“用在刀刃上”是對一個戲曲導演最低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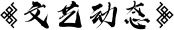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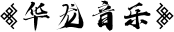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