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秦愛華
天還未大亮,我正處在睡夢與醒來的邊緣,隨著母親響亮的一喊,窗外也隨之熱鬧起來。
首先熱鬧起來的是耳朵。蟬兒老調重彈,一首歌唱了千年,執著又乏味。歌聲里有著人到中年的平淡與固執,卻又帶著無法忽略的憂傷和寂寞,拖著長長的尾音和顫音,從清晨唱到午后,從午后唱到日落。它仿佛從未挪動過位置,也從未變換過姿勢。稍遠的樹冠里另一只蟬仿佛聽懂了它的故事,回應了一嗓渾厚粗獷,只是太過短促。它還未來得及反應,愛情就這樣結束了,只好繼續彈那一天或一輩子都沒變過調的曲兒,也不管你厭倦不厭倦。
斑鳩最喜歡對山歌。“咕—咕咕!”對面山頭的斑鳩亮了一嗓子,見沒人理它,又繼續重復著這支旋律,單調且毫無起伏。當你以為它黔驢技窮時,卻突然吐出一串渾圓舒緩的“咕咕—咕咕”,低沉而綿軟,這低語呢喃,這綿綿愛意,像清泉淌過我的心田,當然我知道它不是唱給我聽的。忽然它又換了支激昂的曲調“咕咕咕—咕、咕咕咕”,連接得那么絲滑,轉換得那么自然,每個音節之間幾乎沒有過渡,那急促而熱烈的告白,那汩汩噴發的熱情瞬間激蕩著我。聽懂的一定還有左邊山腰的雄斑鳩,它渾厚的男中音“咕咕—咕咕”剛起了個頭,“歌手”們就陸續趕來了。背后山頭、左邊山頭,此起彼伏的都是斑鳩的歌聲,像極了多重唱,竟讓我一時不知聽哪兒才好。
隨后出場的長尾巴帥鳥一定是來搞怪的,五音不全地丟下一長串“嘰嘰—嘰嘰—嘰”嘶鳴,還不忘展開剪刀似的尾翼,雜技演員般跳躍在樹枝間。父親說老家人叫它糞池雀,我想它一定是愛停留在糞池的頂端,否則那么英俊的鳥雀怎會有個如此不堪的名字呢?
緊接著我的眼睛也熱鬧起來了。伴隨著嘶鳴,十幾只駕著薄薄羽翼的蜻蜓,如小型戰機般沖過壩子里曬著的紅辣椒,沖過裝著南瓜子的筲箕,沖過忙碌奔跑的蟻群,沖向地壩邊一架茂密的葡萄藤。那陣形甚是好看,領頭兩只并駕齊驅,中間三五成行,斷后的一只憋足勁兒俯沖,好一幅有序有力的沖鋒圖。打頭幾只輕輕點了點葡萄葉尖,旋即又彈飛起來,點水般停留在另一葉尖,余下的卻馬不停蹄奔赴對面的菜園。
空隙處,一只黑衣女神——蝴蝶正盛裝候場,它屏息凝神地立在無花果樹翻開的葉片上,音樂前奏剛過,便妖嬈地扇動著翅膀,那婀娜的身姿、黑色的裙袂嫵媚地擺動著。突然兩只不知名的鳥兒竄出來搶鏡頭,傾情演繹著一場美女與野獸的故事。當斑鳩激昂的曲調再度響起,它立刻又換了個豪邁的舞步,一頭扎向檸檬樹梢,奮力扇動著翅膀,一邊扇一邊還抬頭得意地看我。
正在這時,母親端著一簸箕辣椒出來,笑瞇瞇地說:“這段時間鳥雀還少了很多。如果你清明節回來,看到的鳥更多。比如全身焦黃的黃斑斑鳥喊著‘拉和拉拉,下河去么’;竹雞一大群一大群地在竹林下發呆;布谷扯著嗓子叫‘布谷布谷,快快播谷’;還有一種叫不上名字的鳥,老喊著‘湯包大叔,湯包大叔’;狗餓雀總是‘狗餓狗餓’地吵著,陽雀‘貴—貴—陽、米—貴—郎’地鬧著大家去插秧;甚至還有盆子大的巖雞,黑白長尾巴的三叉鳥……”盡管母親從未讀過書,卻讀懂了大自然這本無字之書,說起這些鳥兒如數家珍,從外形、傳說到鳥名的含義等等,或許母親叫的鳥名和實際的鳥名不盡相同,但母親顯然管不了那么多,早就和這些鳥兒融為一體,并深愛著它們。說話間,地麻雀就在地壩里啄她的糧食、山雀在樹杈上對她呢喃,她任由它們自由自在,還喊我快看那疾馳而過的青菜倌雀。它們就像她的孩子,飛在田野里,飛在山林間,卻怎么也飛不出她的眼和心。
漸漸地,太陽伸出手,一會兒撫摸著我的腳,一會兒又輕撫我的頭,幾下就把我從地壩斑駁的樹影里趕到了隔壁二姑家的街沿上。大約十點鐘的光景,除了熱愛演奏的知了,一切都靜下來了,斑鳩不叫了,蝴蝶不見了,蜻蜓也躲起來了,就連我也躲進了屋子里。
作者簡介:

秦愛華,豐都縣第一小學校語文高級教師。重慶市優秀班主任宣傳人選、重慶市家庭教育高級指導師、豐都縣家庭教育講師團講師。曾在《人生十六七》《愛情婚姻家庭》《班主任實踐與探索》《教育評估與監測》《豐都日報》《豐都教師》等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三十余篇;出版過個人專集《放飛手心的幸福——愛華教育故事選》;縣內做家庭教育講座68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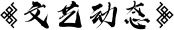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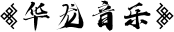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