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 何雨軒
數(shù)字技術(shù)的浪潮裹挾著人類步入一個(gè)前所未有的社交圖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但可以克服時(shí)空障礙,并且能夠通過微信消息還原語言,視頻通話還原相貌,VR還原現(xiàn)實(shí)場景。在這個(gè)“永遠(yuǎn)在線”的時(shí)代,北京大學(xué)邱澤奇教授的《重構(gòu)關(guān)系:數(shù)字社交的本質(zhì)》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shù)刀,剖開數(shù)字社交的肌理,用生動的案例揭示其如何重構(gòu)人類社會的基本關(guān)系—家庭、朋友、工作與生活,為理解數(shù)字社交的本質(zhì)提供了兼具理論銳度與現(xiàn)實(shí)溫度的新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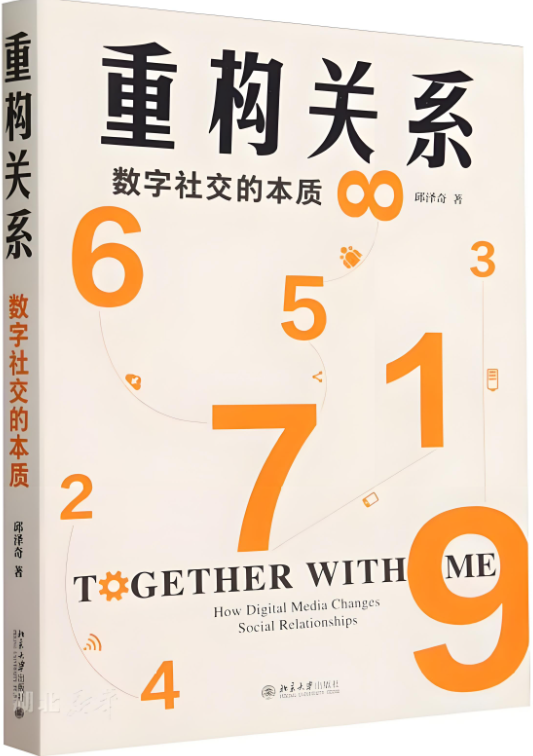
從“身體在場”到“數(shù)字同場”的關(guān)系建構(gòu)
在未有文字記載的早期人類社會中,人際間的具身化交流局限于物理空間的范圍之內(nèi)。隨著文明的進(jìn)步,文字作為物質(zhì)化的交流媒介應(yīng)運(yùn)而生,它使得信息與思想借助符號的力量,得以跨越地理上的重重障礙,實(shí)現(xiàn)了遠(yuǎn)距離的傳播與交流。而數(shù)字時(shí)代的連接泛在,徹底消解了時(shí)空桎梏,使個(gè)體得以編織一張以自我為中心的全球關(guān)系網(wǎng),個(gè)體與社會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以個(gè)體為中心進(jìn)行資源組織”正在成為新的個(gè)體與社會關(guān)系的特征。在連接泛在前提下,個(gè)體可以隨心所欲地與世界上的任意對象建立關(guān)系,當(dāng)然,人們對數(shù)字技術(shù)的過度依賴,也引發(fā)了一些學(xué)者的擔(dān)憂。
從表情包到視頻通話再到虛擬現(xiàn)實(shí),人們不斷利用愈發(fā)先進(jìn)的技術(shù)模擬身體,以緩解身體不在場的缺憾,彌補(bǔ)情感表達(dá)的缺失,但這種身體缺席的交流仍然引發(fā)了焦慮和不安。雪莉·特克爾曾在《群體性孤獨(dú)》一書中曾向社會發(fā)出警告,認(rèn)為數(shù)字技術(shù)重創(chuàng)了人們的情感與心靈,帶來了“情感泡沫”。針對特克爾的悲觀論調(diào),作者提出了更加樂觀的視角。他質(zhì)疑將“身體同場”視為實(shí)現(xiàn)群體性的唯一路徑,指出“數(shù)字同場”亦是滿足人類群體性需求的有效路徑。在書中,何瑜通過電子郵件開展“碼里戀愛”,建立屬于自己的親密關(guān)系;施翹不斷適應(yīng)數(shù)字交流規(guī)則維系與男友的親密關(guān)系;許俊熙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進(jìn)行語言cosplay滿足了自己的興趣追求;高考失利的程慕馨利用數(shù)字鏈接突破了科層崗位,擁有了更多可能性。在自我社會下,個(gè)體圍繞社會的社交轉(zhuǎn)變?yōu)閭€(gè)體匯聚關(guān)系的社交,技術(shù)給予了個(gè)人與任意對象建立關(guān)系的機(jī)會,并使得個(gè)人能夠在自我建構(gòu)的關(guān)系中獲得自身期望得到的價(jià)值和意義。
技術(shù)賦能與功能異化的思考
技術(shù)發(fā)展具備雙重性,一方面是技術(shù)的賦能,年輕人通過算法匹配“搭子”,精準(zhǔn)滿足健身、觀影等細(xì)分需求;職場人士掙脫地理束縛,在云端構(gòu)建跨國協(xié)作網(wǎng)絡(luò);獨(dú)居老人借助數(shù)字設(shè)備,將“每周探望”升級為“時(shí)刻在場”。另一面則是異化的暗流,朋友淪為功能模塊,親密關(guān)系退化為情感代餐,工作以“隱形加班”侵蝕生活邊界。當(dāng)關(guān)系成為可定制、可替換的“數(shù)字零件”,情感的深度與重量或許便悄然消逝。
面對數(shù)字社交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作者提出“建構(gòu)積極和包容的生活關(guān)系”。正如社會人類學(xué)教授項(xiàng)飆“重建附近”的呼吁那樣:在迷失遠(yuǎn)方的搖擺中,從具象的、周邊的生活中重建交流與互動,來汲取一些前行的力量。患口吃的陳妍通過舞蹈社的微信群重獲表達(dá)自信;肢體殘障的白彩鳳通過直播建構(gòu)了自己的生活世界;雙目失明的裴子欣通過線上心目影院找到了同齡伙伴;數(shù)字移民張秀梅接納數(shù)字技術(shù)找到了自己的老年生活新陣地。書中的一個(gè)個(gè)鮮活案例揭示了一個(gè)道理:技術(shù)本身并無善惡,數(shù)字技術(shù)下的個(gè)體并非完全孤獨(dú),關(guān)鍵在于個(gè)體如何把握技術(shù)這支“筆”來敘寫何種生命價(jià)值與意義。
在數(shù)字浪潮中錨定自我
人類社會正經(jīng)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度媒介化進(jìn)程。智能設(shè)備成為“新器官”,AI技術(shù)不斷進(jìn)化成為“第二大腦”,算法的濫用異化了人們的思維,交往甚至勞動……人類浸身于信息的海洋中,一舉一動所留下的數(shù)據(jù)都如滴水歸海,偏見、焦慮、不平等在數(shù)字暗流中悄然顯現(xiàn),人的主體性受到了巨大沖擊。這提醒我們,數(shù)字技術(shù)重塑的不僅僅是社交關(guān)系,更是人類的存在本質(zhì)。就像韓炳哲在《非物》中講到的那樣,“我們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球和數(shù)字云之中。”信息的流動和去形化使得一切變得虛無縹緲,任何東西都失去了牢靠樸實(shí)的手感,數(shù)字技術(shù)剝奪了身體感知的交流,讓真實(shí)的面對面消失于無形,只剩冰冷的數(shù)字和代碼。
然而,面對數(shù)字浪潮下的各種變化,無需恐懼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正如作者所言:“對生活關(guān)系的重構(gòu),不是奔向自由與獨(dú)立的欣喜,而是形塑人類新生活的機(jī)會。”個(gè)體如何選擇,決定了他們的道路是通往孤獨(dú),還是通向幸福。或許真正的自由,在于清醒認(rèn)知技術(shù)的賦權(quán)與帶來的挑戰(zhàn),在“連接泛在”的海洋中,以主體性為錨點(diǎn),編織一張既積極包容、又保有溫度的關(guān)系之網(wǎng)。身處數(shù)字時(shí)代浪潮的我們,不僅要成為技術(shù)的使用者,更要成為其創(chuàng)造者和引領(lǐng)者。通過不斷反思和探索,在科技賦能下,尋找到屬于這個(gè)時(shí)代的生命意義與價(jià)值。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這場前所未有的變革中,錨定真正的自我。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