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 何芝娟
“記憶是活生生的生命,處在持續的生成之中,對‘記與忘’的辯證關系始終開放。” 這是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留下的箴言。提起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慘痛記憶,我們常強調“不可忘卻”,但現實的復雜超越了記憶與遺忘這一組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因為“歷史不會自己說話,它只能依靠人們的言說”。李紅濤、黃順銘合著的社會科學著作《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一書便是從這里出發,以史為經、以不同媒介場景為緯,考察南京大屠殺創傷建構與記憶形塑的互動過程,帶領我們思考:如何反思我們建構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實踐?為建設面向未來和光明的民族共同體,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南京大屠殺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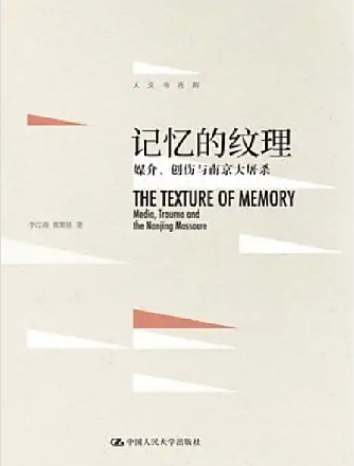
撕開傷口:歷史在媒介中被書寫
本書開篇就對各個階段里南京大屠殺媒介記憶書寫進行了細致的梳理。1937年,西方記者在報道南京大屠殺時稱其為“地獄般的四天”,將這場暴行首次帶入全球視野。國內報章《大公報》則發布社評《為匹夫匹婦復仇》,這是對日方侵略者暴行的憤怒控訴,也是戰時進行民族情緒動員的重要工具;戰后審判中,對受害者人數“20萬+”與“30萬+”的討論則更加體現出話語權的爭奪;在冷戰陰影下,這道記憶傷口經歷了荒誕扭曲,淪為斗爭的工具;中日建交時,卻又被強行貼上“友好”的創可貼,在“中日友誼”的敘事中被淡化;直到1982年日本教科書事件,這段無法被國人忘卻的傷口才被重新撕開,并在《人民日報》的“恥化報道”中與民族復興相結合,再次出現在公共視野。及至當下,國家公祭日正式創立,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創傷記憶以一種制度化的形式作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不斷鞭策著后人勿忘國恥、我輩自強的心志。
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在這八十多年的流轉中不斷變形:最初,它是幸存者難以啟齒的個體記憶,是地方層面的傷痛;后來,它上升為國家記憶,成為民族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它已被納入“世界記憶”,被寫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檔案。戰時的媒體強調“復仇”,戰后的法庭訴諸“正義”,新中國成立后則突出“國恥”……每一次敘事的重組,都意味著遺忘與記憶的重新分配。
作者通過對這段歷史的梳理提醒我們,這一路徑并非只是自然沉積的歷史事實,在媒介的書寫中經歷著復雜的變形與重構。的確,因為事實的殘酷往往超出語言的承載力,媒介對于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書寫更像是一道被反復撕裂又不斷縫合的傷口,這種書寫一方面是創傷得以進入公共視野的前提;另一方面也注定了它始終處在被再造的動態之中。每一次敘述既是對遺忘的抗拒,也是一次新的詮釋與再思考。
數字嬗變:紀念的莊嚴與輕盈
進入數字時代,對南京大屠殺的紀念與記憶建構也拓展到了數字互聯平臺。書中對此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一方面,我們不可否認,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的發展進步讓莊嚴沉重的紀念儀式變得更加“輕盈”了。這種“輕盈”首先體現在紀念參與的便利化。比如參與方式的革新:線上公祭活動打破了時空限制,讓全球網民得以通過“虛擬捐磚”“數字點燭”等方式參與紀念。在“捐磚行動”中,參與者只需輕點鼠標就能完成祭奠儀式。數字技術的便捷性極大拓展了記憶社群的邊界,使紀念活動從地方性儀式轉變為全球性實踐。
另一方面,這種“輕盈化”卻可能帶來記憶深度的流失。在短視頻平臺上,三十萬生命的沉重歷史被壓縮成10秒的“淚目視頻”,甚至只是幾秒鐘閃過的一張全黑圖片,用戶輕輕劃走,隨即沉浸在下一個娛樂視頻的感官刺激中。記憶的“快餐化”一點點地消解歷史的厚重感。而更隱蔽的危機在于算法對記憶的馴化。短視頻平臺根據用戶偏好推送的“歷史爆款”,往往強化單一敘事模式:或是血腥影像的重復刺激,或是口號式的愛國表達。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12秒水滴裝置(象征每12秒一個生命逝去)被簡化為15秒的“淚目視頻”,記憶的厚重感正被流量經濟的碎片化邏輯消解。當短視頻平臺將歷史創傷與其他娛樂內容并置時,記憶的莊嚴性可能被消解為信息流中的普通節點。例如,用戶前一秒為遇難者“點燭”,下一秒便滑向搞笑視頻——這種認知斷裂暴露了數字記憶的脆弱性。
作者在書中的種種分析無一不在提示我們,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在數字時代的命運最終取決于我們如何平衡“輕盈”的傳播力與“莊嚴”的反思性。當技術既能降低參與門檻,又不稀釋歷史重量時,數字記憶才能真正成為對抗遺忘的利器。
記憶回響:多元敘事與全球對話
《記憶的紋理》始終將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視為一塊被不斷書寫、不斷打磨的木版,而非靜止的石碑。正如書名所昭示的,“紋理”既是時間留下的印記,也是多重力量交織的產物。書中通過剖析記憶與遺忘的辯證關系,勾勒出歷史與現代交織下的記憶紋理,其深層目的在于回答一個時代命題:在多種力量相互纏繞的記憶場中,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建構南京大屠殺記憶?
對此,兩位作者在書中反復強調多元敘事。比如,作者強調多元敘事的必要性:司法的“起源話語”、民族的“紀念話語”、國際倫理的“譴責話語”與對抗日本右翼的“回應話語”,共同構成了一個復調場域。這提醒我們,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不能局限于某一種敘事模式,否則要么流于政治化,要么淪為符號化。真正的挑戰在于,能否在多聲部中保持敘事的開放性,而不是讓單一的強勢敘事重新獨占解釋權。
此外,此書還站在全球記憶的高度,審視南京大屠殺記憶上升形成“全球記憶”的可能性、阻礙與動力機制。這一洞見打開了我們的視野,明確了南京大屠殺記憶所面臨的雙重使命:既要守住莊嚴與厚度,又要面向跨國對話與代際傳承。這一視角在現實中也獲得了生動印證——2022年,美國明尼蘇達州典當行主埃文·凱爾發現并公開捐贈的侵華日軍罪證相冊,正是跨國記憶對話的典型案例。這位普通美國青年通過社交媒體引發的全球關注,既驗證了歷史記憶超越國界的傳播潛力,也展現了民間力量在突破政治藩籬、重構歷史認知中的獨特價值。
對話的張力不是缺陷,而是記憶生命力的來源。當凱爾的相冊與南京紀念館的檔案形成跨時空對話時,我們看到的正是南京大屠殺記憶超越國家民族,成為全球記憶的雛形。換言之,本書的貢獻在于提醒我們:記憶不是通過一次性方案被“解決”的對象,而是需要不斷在政治、媒介與倫理的交錯中被重塑的過程。從《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戰地報道,到埃文·凱爾的相冊捐贈,再到維基百科的編輯爭奪,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始終在動態重構中保持其警示意義。這種既扎根民族歷史又面向人類共同體的記憶實踐,或許正是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守護歷史真相的最佳路徑。
總的來說,《記憶的紋理》一書兼具理論與實踐意義,不僅為南京大屠殺研究提供了創新的媒介分析框架,更對當代社會的記憶政治提出了深刻反思。該書通過細致的史料爬梳與前沿的理論對話,展現了歷史記憶如何在媒介技術的演進中不斷重構,既揭示了權力對記憶的形塑機制,也為平衡記憶的公共性與個體性、全球記憶建構等提供了建設性思路。其價值不僅在于解構既有的記憶敘事,更在于啟示我們:唯有保持記憶的開放性與反思性,才能讓歷史創傷轉化為面向未來的精神資源。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